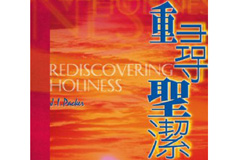讀書樂
告慰雪芹:慰芹廬文存
張之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
幾年前,張之先生的巨著紅樓夢新補出版,洵為中國文化界的一大盛事。本人當時未得躬與其盛,是後來才得以讀到,憬於作者功力之深,了解曹雪芹之廣,考證研求之精,嘆為觀止。
就愚見所及,現今世上,沒有別的人能夠續成這部巨籍。多年來,紅學流行,好些人都想“染指”,卻不都具備充分的條件。就如新文化的領袖胡適,他的名夠高,也會作考據,只他研紅而不“知音”;意思是說,他對音律了解不夠,對原作者的心意,也難有深的體會,所以無以談續。其他的人,要通詩文而有考證根基的,中國雖大,其人卻屈指可數了。
文存收集的文章,作者以為大部是補紅的“副產品”,其實,價值還超過許多。從這些文章中,可以了解當時文壇的境況,作者個人的經歷,可以作史料看,也可以知道作者的心路歷程,未嘗不是一把辛酸淚。
時人喜作回憶錄,有不少是自己鼓吹,真正可憶者不多。張先生有如此成就,卻沒有甚麼表功自衒的意思。他敘述其續紅的經過,是一件很動人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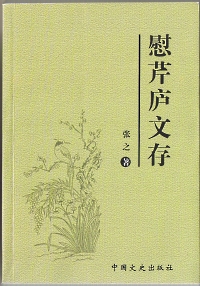
張之先生名其居曰:“慰芹廬”,似乎是雪恥洗冤的口氣,以求告慰曹雪芹,可見立心之高,要成就雪芹遺願;致畢生之力,作此扛鼎鉅業。只是生當斯世,經過“除舊”,“反右”,各樣風波,懷璧十年,而秉其初衷,終於完成,歷盡艱難,可想而知。慰芹廬文存的文章,有的雖然已經見於新補,有的已經在不同學術刊物發表,得以收輯問世,更為合宜。因為其中有懷舊,紀遊,考據,論詩韻等,皆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因此本書刊以行世,對這樣的有心人來說,是可喜的事,對於讀者來說,自然更是如此。
作者不僅是出自個人興趣,更以續紅為職責,仗義為之。要“撥高續之亂,反曹著之正。”(頁6)他以為脂硯齋批,是紅樓夢作者的本旨;而“程高一類人,便撇開脂批所示,另立爐灶,別續四十回。”(頁5)對於“脂批提示後回之數十事,高續中卻一事也無!”(頁4)這樣改編刪接過的東西,偏要頂着原著者的名字,怎不氣人?
剽竊,是把別人的東西,原非自己所有,攘為己有;高鶚的作法,則是把自己的意見和作品,嫁接給別人,是反向的“剽竊”,不是竊他人的文字,而是竊他人之名。這樣的作法,自然並非常見,乍看也似乎不是大惡,其假借他人名義,並不是誠實,則與剽竊初無二致。所有張先生為愛藝術,為張正義,才奮筆補書。他說:
我愛曹雪芹的紅樓夢,我崇拜曹雪芹。我愛的東西缺了角,我想把它補完整;曹雪芹的真意被歪曲了,我想把他的真意寫出來。所以,我雖淺學無文,還要斗膽為曹公補書。(頁9)
這番誠意,正氣,確是值得推許的。
張文中引敦敏贈雪芹句:“愛君詩筆有奇氣”,並說:“知君詩膽昔如鐵,堪與刀穎爭寒光。”(頁67)如果“詩以言志”的話,在此可以適用,從詩了解書中人物,以至著者心意,該是自然的事。
曾有人評法國印象派的畫,是從心裏畫出來。其實,這該是一切藝術當奉行的原則,發之於心,才不流於皮相。張先生對於紅樓夢,也是從心裏讀出來,續紅樓夢,也是從心裏着手,生發出來。更重要的,是他對音律了解之深,研究之精,可以直參雪芹心意,領會“按頭製帽”的妙手絕技。其實,作者不僅看準了頭,也看準了頭腦裏的思想,才可以使詩與思想配合得天衣無縫。這不是僅鑽研故紙,作考據的人,所可望達到的境界;必須如先生對詩律探深體微,才作得到的;紅樓夢問世兩個半多世紀以來,無人能達到,甚至少人敢作如此想,而張君敢於操筆,實在是文學史上的壯舉。因此,如果說張的文才,近於原作者曹雪芹的水平,也不算是過譽之辭。文學作家兼理論家殷穎先生,說張先生的續紅,亞於原作者曹雪芹,而凌駕程高之上,的是持平的說法。
在文存集中,有“紀念鍾彥師逝世一周年”文,作者自記“句邊彩筆神奇化,詩國金鍼仔細論。”如此念舊懷師,真摯感人,現代人中可謂少見。這樣的品德,已值得效法(頁304-306)。只是不知他當時向華鍾彥的原因,是為學詩而學詩,或是為攻紅詩而學詩,以求進窺堂奧,文中不曾詳言。但這種認真與虛心求進的精神,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作者也稱述“華師教詩教人”,要他“存心為人民服務即是。”秉持原則,可以“不識時務”。作者說:“為人民服務云云,眼下多已不講,余卻奉之維謹。蓋不僅當年風尚如此,且是吾師所諄諄教誨者也。”他學為詩之外,也兼學為人。時人只為利益,不重道義,叛師背道,已經算不了一回事,這精神何等可貴!
因此,希望讀此書的人,不僅是學得知識,不僅是學得詩文的技巧,也能夠學作者的作人。(亞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