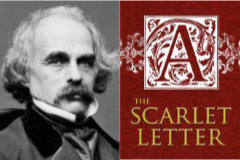打鬆美盤得大自在
美盤是一種完美的結構,如果有人敢冒美學之大不韙,要打破這個完美的組合,應為煞盡風景,反叛美學,破壞藝術,走向美的反面,便淪為醜惡了。這種行徑所為何來?這樣能得到“大自在”,實在是太離譜了。但出此語者,卻為一位清代書法怪傑與寫竹大家,人稱“揚州八怪”之首的鄭板橋。他這略帶禪意之語究係何意?
無論何種可稱為美的藝術,都有規律,如西樂中嚴格的對位法。無論中,西樂採用的五音階或七音階,均各有其音律,違反此律,便成為噪音,無美可言了。
當今最前衛的音樂,所演奏出來的幾乎都是噪音,將大量噪音以超高分貝的音響播出,要強迫灌入人不設防的耳朵中,強暴凌虐的塞進人的聽覺,如酷刑無異。人的聽覺遭受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藝術云乎哉!美感云乎哉!
繪畫亦如此;無論中,西都不能例外;歐洲的畫風迭經多次變革,各大家皆獨樹一幟。歐洲畫壇的宗師無數,各具特點,各領風騷,也都美不勝收。但要緊的各有不同形式的美;如果將藝術的靈魂抽離,便無法找到美;如畢卡索有些畫作將人的五官易位,雖有他的怪異畫觀,卻看不出美在哪裏,實在難以茍同為美術。當美術繪入現代的抽象畫,雖沒有定格,沒有主題,但也不能離開美的特質,如隨意在畫板上擠一些古怪的油彩,再不經意地移植在畫布上,不知由哪裏可以抓到一點點美感,甚至連猩猩,大象,貓,狗也可作畫,難道繪事已淪入畜道了嗎?這是否太離譜了。
美盤可以打鬆,絕不能打破,回到混沌的雜亂中,怎可稱之為藝術?又怎能再體認出美感。
再以科學為例,物理學也講求對稱之美,所謂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即方,圓皆為美,都為一種美盤的安排,這種美的組合豈容打破。何以鄭板橋卻敢造次,難道也有他的道理嗎?
藝術家所認同的黃金切割律,便為美學規律之一,而造物主所鋪陳的日月星宿,星羅棋布,整個宇宙的運作,皆有其定規。如一旦失序,宇宙便會大亂,天體便崩壞了。這一切都是冥冥中所安置的美盤。
以人格為例,魏晉時代的文人士子們尚清談放任,不修邊幅,放浪形骸,以飲酒賦詩為正業。王羲之的“坦腹東床”為一個好例子,但此種放任也有一個尺度。如三國時代的狂士彌衡,便太超過了,他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裸露胴體,並且“擊鼓罵曹”雖能逞一時口舌之快,卻招來殺身之禍,真是何苦來哉。而人格的“格”字不就是一種行為規範嗎。
按美學多半都講求嚴格的規範,如中國古詩中的格律,韻律與對仗,平仄都有規矩,反之則不成為古詩了。
以詩而言,由詩經的四言詩,演進到盛唐的五言古詩,樂府,律詩及絕句等,唐詩已發展到詩的巔峰,到宋代轉折為詩餘之詞,詞人輩出,詞之淒美,可吟到斷腸,在詩以外另樹高峰。進入元代之曲,雖為詞餘,不僅可低回吟唱,再加上舞台的表演融入綜合藝術的境界了。湯顯祖的“牡丹亭”正是此例之說明。當詩的腳蹤步入近代,又有更顯著變革,詩的文字已採用白話文,民初誕生了最早的白話詩。早期詩人有胡適,徐志摩等啟蒙詩人,領一代風騷。白話詩再往下傳承,便出現了今日的現代詩;詩的美盤不但打鬆,有時還被打散了。五四運動標榜詩的再革命,但一不小心,也會變得讀起來讀不懂了。甚至有人說,你將一版鉛字打散,再隨興排列成散行,便可稱為現代詩。而人讀不懂才可稱為現代詩,這樣便走火入魔了。美盤打散且打亂,便甚麼詩都不是,詩的語言形式無論怎樣改,讀起來都應該像詩。形式無論如何變更都不要緊,詩的靈魂是美,詩如缺少了美,便抽離了詩的靈魂,美盤可以打鬆,但不能打亂。

鄭板橋畫像
板橋的“六分半書法”與“亂石鋪街”格式,正是打鬆了美盤的具體例證。但他並未“打散美盤”或“打破美盤”,否則其書法便不會成為一代宗師了。

鄭板橋書法作品
若將“美盤”提高到神,哲學境界,便是一個簡單的“誠”字。中國儒家將“美盤”提高到抽象境界,認為“誠”實為最美,誠(中庸.二十四.天道),是一切美好的最高歸依;“誠”為天地之間一切道德規律的總綱。但可惜人卻在樂園中將美盤打得粉碎了。所以人便缺少了這個“誠”,也便缺少了美。要將這個破碎的“誠”之美盤,再回復舊觀,讓人們回復到初受造時的誠實之美,只有一途;就是要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上流血的救贖代價,才能將破碎的美盤回復神造人時的原創之美。
當基督在十架上說:“成了”的時候(約翰福音19:30),這個被打碎的美盤,便已回復到神原創美好的最高境界,人才可以回復到真理的“大自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