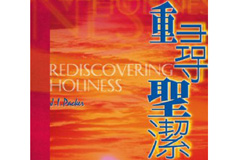魚,魚

我在香港長大,喜歡吃新鮮的游水魚,淡水魚或鹹水魚均不苟。到北美洲以後甚麼都得將就些,曾到一些連醬油都難買到的地方去進修,自然講不到要求吃“活魚”了。記得那是將近聖誕節的時候,我決定要好好的款待一下自己,去找一找超級市場有沒有“雪藏的魚”,以補償那些日子以來的缺魚之苦。找來找去,終於見到一個“Fish”的牌子,在那裏放着一包一包的東西,我看來看去怎樣都不像魚,而是好像我們中國人的“大菜糕”,透明,無色,又像外國人的飯後甜點果凍Jelly;我還把那部長找過來問個清楚:這個到底是不是魚?他說:“是魚,那是Lutefisk。”我高高興興地買回家去,心想這下可好了,這兩塊魚我可分兩餐,用點醬油拌一拌,灑兩滴麻油,然後用電飯鍋連米飯一蒸,便有“蒸魚”吃了,想着想着不覺垂涎三尺,加快車速回到宿舍便去行動。飯好了,魚熟了,聞到飯香卻無“魚腥味兒”,這倒怪了,不理了,肚子太餓了,自己“開檯”吃飯去,嗯!不對,這魚怎麼還是透明的?難道沒熟?不可能吧!好,我停筷又再開火去用鍋來煎魚,以我煎牙帶魚,紅衫魚,瓜核魚,大魚等等的經驗,我就不信“煎”不熟你。搞了半天,它就是“不變”,我拿筷子去夾一口來吃,真不是味道。連續幾天下來,我就是不服氣,用不同的方法想去“搞掂哩個魚!”我燜它,烤它,煮它都不行,它就是那個樣,死德性,半透明的不熟,而且吃而無味。我真不開心,不明白這是甚麼外國魚嘛?

過了幾天,我在醫院當班不太忙,於是就跟一個護士談起我的“聖誕魚”之經驗,我問她:“這是甚麼魚嘛?蒸,煎,炒,煮,烤都不熟,也吃不到嘴,這是怎麼搞的呢?是否你們本地人有特別的方法做魚呢?”她問我:“你買的是甚麼魚呀?”“我買的是Lutefisk。”她笑得彎腰駝背,眼淚直奔;我卻氣壞了,怎會有這麼沒有同情心的護士?別人低聲下氣請教,加上煮魚不成的挫折,竟還要笑…我在肚裏咕嚕着,忽然她止住笑,直起腰來,邊抹眼淚邊跟我說:“我們本地人也很少吃這個魚的,這魚是新鮮由挪威運到的,是傳統挪威家族聖誕餐不可缺的一味。那是用煎熱的牛油,在油中燙一燙,就放在口裏吃的。從來沒有人像你那麼大費周章地去烹調,哈哈哈…”她又開始笑個不停,自此這“烹魚”笑話傳遍整間醫院,我也為自己不屈不撓的研究精神鼓掌。
註:“Lutefisk”通常包裝成“包”,水滾一燙快起,放特別香料加牛油或酸奶油(Sour Cream)食用,現代年青一代的北歐移民少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