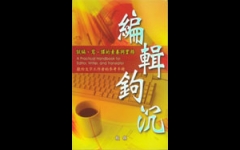文字事工的心靈傳承
仍然記得,我決定自一手創建的“道聲出版社”辭職,急流勇退當天,我宣告要辭去社長職務時,有一位道聲老同工不禁驚訝地說:“這個消息太讓人震驚了。”我說:“其實今天報紙上的頭條才是一項震驚世界的消息:埃及總統沙達特在檢閱軍隊時,被一個士兵舉槍刺殺了!我辭職只是小事一樁,不值得大驚小怪。”
我由道聲離職時,正值道聲業務鼎盛之際,我及時抽離,應是最合宜的時機。事後我再三表示:上帝使用一個人,都有一定的時限,進退各有定時。
辭職後,我交代同工將道聲社務交給當時的台灣信義會監督,因董事會還未任命新社長。不料此後,長達四十幾年,“道聲出版社”始終沒有一位全時間的社長,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我辭職離去,並未親自辦理移交,是由道聲同工代理,因皆為硬體移交:即賬冊,現款及庫存書籍等,均可點交,我無須親自出席,移交清冊列出,我簽名蓋章即完成手續。
未想到過了四十多年,“道聲出版社”的文字事工,已由大陸時代算起到2013年,轉眼已經一百年了。我應邀寫了“中國基督教文字事工的遞嬗與當前的挑戰”一文,刊於台北道聲百周年特刊文傳百年,為道發聲紀念刊上。因此,我辭職也早已成為歷史檔案了。
與道聲同工的一席話
2015年3月17日晨間,現任道聲出版社社長陳志宏牧師(四十餘年後之首任全時間社長)邀我在當天道聲出版社靈修時間,對道聲同工講幾句話。我想這應是我在“道聲出版社”對同工的最後發聲了。
我於2015年春天返台的主要原因,是要辦理我在台灣一些最後的事情。若無神的恩典,我根本不可能成行,因我還帶着一身病痛。
在踏上歸途的前幾天(三月十七日),我對道聲同工所講的勉勵之言,其實也就是我離開出版社後的一次“心靈傳承”(軟體移交)。當天上午在座的二十幾位同工,我熟悉的並不多,半數以上是新面孔。但才講了開頭的“作忠心的管家”序言一半時,便有位新同工已忍不住伏案淚崩了。接着不少同工也都相繼飲泣,並有幾位新,老同工上前來與我相擁而泣。所以當天我想講的內容,並沒有講完,但也難以為繼了。如今只好將我當天講話的內容再整理一下,筆之於書,以完成這個“心靈傳承”。
以下是摘錄當天道聲同工曾家瑋編輯的個人部落格文字:
這一堂課絕對是“編輯人上課筆記”最重要的一堂課。上個禮拜,就期待今天早上的到來,從來沒有這麼想要開會的感覺。因為我知道,這或許是最後一次見到老社長殷穎牧師。自1973年,道聲出版社在台灣正式成立,殷牧師是第一任社長,帶領道聲走過一段風雨,推出“百合文庫”,廣受大家喜愛。1982年,他從社長職務退下,仍持續文字工作,六十餘載從未間斷過。
昨晚一直在回想老社長的每一句,記錄的過程中也是鼻酸啊。
今早的衝擊很大
老社長的勸勉,我更確信就是該抱持的理念
這也是我常常不斷跟社內主管再三強調的
沒有理念,出版就不是出版了
老社長兩次向全社員鞠躬致意,致謝
每鞠躬一次,我就落淚
他說,這次來台是交辦後事
可是,我們承接得下來嗎?
我們承接得起出版的異象和使命嗎?
老社長一開口說話,我就趕緊找機會攝影留念
深怕沒有下一次碰面的機會了
人才和歷史,是機構,團體,組織最重要的資產
但是,卻也最容易被忽略和輕視
我不曾與老社長共事過
卻何其有幸能聽他兩次的分享
我推開鍵盤,關掉螢幕
拿出紙筆,寫信給殷牧師
謝謝他的付出,謝謝他的勸勉
若可以,真希望能夠還能聽到他下一次的分享
老社長離去,留在社內的我,該做甚麼…
“先器識,後文藝”
虛華的文宣品,不是出版
“先器識,後文藝”,再來談成本會計
沒有器識,沒有文藝氣息,如何談成本會計?
浮誇!
文字工作者及出版人,肩負的使命很重大。即使社會上文化界一個普通的出版者,對整個人類文化使命,也非同一般;若只是為了要賺取一些利潤,不如改選其他職業,賺錢才比較容易。但踏進文化這塊田地,便應有比一般人更重的道德責任感。若不顧這種使命,而盲目地去印一些書賺錢,便會違背文化道德,日後必然會遭受自己良心的譴責。而身為肩負傳揚福音使命的出版人與文字工作者,其責任自然更重。在進入實質的出版事工(“文藝”)操作之前,必須要有完全的準備,因其所經營的,是傳揚福音與造就信眾的千秋大業。如僅以口傳,語言可隨時間消失,但若出版成為文字書刊,則成為永恆的天業。

李提摩太
故作為一個基督教出版人,必須要先有充分的預備,才可肇始。
我最先向李氏學習到的,是基督教出版物必須要對社會大眾起領導作用,絕不可成為一般出版界之驥尾。即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必須要站上一個制高點,發揮對全人類社會的啟導作用。如萬一無法達到上策,至少也能得其中策,但若僅可“取法乎中”,最後,便只能“得其下”了。基督耶穌便曾教導我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馬太福音5:48)。這是我由李氏學到的第一堂功課,也終身奉為圭臬。
若談到“器識”這個重要的異象時,便應首推唐初文學批評大家,即吏部侍郎斐行儉;按唐朝為一個盛產詩篇的朝代,唐初已出現了一些詩文大家,諸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等人,個個文采風流,文壇地位顯赫。但斐氏對他們的評價卻並不高;他指出:“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的讜論,其實他所推崇的唐代具有器識的詩人,應指盛唐幾位大詩人,如李白與杜甫等;其中杜甫仕途坎坷,終生飽受命運摧折,但卻能磨礪出超人的器識,故其詩作境界極高。李白則為不世出之大天才,“李白斗酒詩百篇”,古今只此一人。他才華驚世,為天縱之才,但也時運蹭蹬,且不幸早逝,所以其器識還不若杜甫,但如論到寫詩的才華,則杜甫遠不如李白。到晚唐後主李煜,攀上唐詩另一高峰,人稱詞聖,詞作哀怨動人,淒豔絕倫,但僅具文采,便不足與語器識了。
作者的德性重於寫作技巧,林語堂大師說:
“一般人寫文章,看重文字的推敲,其實文章本身的修飾固然重要,但作者的思想,情緒,德性更為重要,僅有優美修辭作品,永遠不能列為第一流。由思想,情感,德性構成的作者的性靈與獨特的風格,就成為這個作品的骨骼,沒有骨骼的作品,是言之無物,是不值得一讀的。”(語見林著無所不談合集)
所以人在修習文藝之初,必先着重做人的量度與見識;人必須要修成大智大勇,到達“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亦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語出范仲淹“岳陽樓記”)的心胸。請注意-關鍵字“憂”,“憂”字就是“器識”,心胸要坦蕩如光風霽月,所“憂”者皆為天下蒼生,這不就是基督當初為耶路撒冷哀哭的心腸嗎?出版人有了這種器識再去從事“文藝”,定可體現基督的“大使命”,而不會僅斤斤於小節。出版人要能登高才可望遠,才能具有最大的視野,與向普天下傳福音之情懷與襟抱。
孔子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人先有了器識,“文藝”者其餘事耳。故,“先器識,後文藝”應為一個基督教出版人必備的歷練。
今天我對諸位講這些話,只說明了一件事,即我當初從事出版工作時,雖有此種感悟,但尚未完備此種器識的歷練,後再經四十年時程的磨礪,才略有進境。謹以此與各位及出版界同工共勉。
衝出窄巷
不久之前,接到香港一位出版社編輯函邀,要我寫出半世紀前我初出茅廬,剛踏入基督教出版界時的心靈狀態。
日前接梁美英牧師轉來香港基道出版社梁冠霆編者邀稿函,要我為基道文字撰稿。基道文字四月號主題為“窄巷”;並附上我四十五年前,在香港基督教周報刊載的幾篇文稿,要我撰寫“衝出窄巷”文。我對四十五年前發表的文稿,早已毫無印象,重讀才喚起半世紀前的回憶;對當時教會出版界的種種情景,不勝感概。但今天不已是二十一世的二十年代了嗎?何以教會的文字事工,在這四,五十年中停格了?是時間錯亂了嗎?時間應未錯置,只是今日教會的文字事工仍困在昔日的“窄巷”中,難以脫身罷了。
猶憶當年我以“百合文庫”走出窄巷,打進台,港一般書市場,且因出版物的出色(首採全彩封面,摒棄廉價紙張,印刷與裝釘),讓台,港教會與一般出版界眼睛為之一亮。特別是頭五本書,再版由五千躍至萬本,一月內再版三,五次,才能填飽市場的需求。有一次我帶一位國外教會出版家到當時台北市的重慶南路書店街巡視,每家大門內擺出的第一排書幾乎全為道聲的“百合文庫”,讓這位出版家十分驚訝。“百合文庫”後來還榮獲行政院新聞局評選為傑出出版物金鼎獎。又因出版諾貝爾獎得主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且尊重國際版權,受到當時的嚴家淦總統特別會見,當面鼓勵。
說來難以置信,這套文庫中的編寫譯的技巧一書還曾遭香港書商盜印,我以告誡作罷。當時乘勝追擊,以香港為跳板,將“百合文庫”推進東南亞市場,遍及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銷路也十分紅火,許多年後我經過吉隆坡時,還在一家書店櫥窗裏看到從前關於“百合文庫”的海報。
曾幾何時,教會出版物已榮景不再,重由一般市場中退縮回教會書店的窄巷中。
今天教會出版社何以又回到這個擁擠的窄巷中蹣跚踱步,原因應很複雜,不僅一端。
窄巷,可以靠神的力量拓寬,打通;但若在窄巷中待久了,走不出去,便會成為一條死巷,這才是教會出版界必須特別警惕的。要單靠出版界自己檢討並不夠,教會當局所訂定的宣教政策,每每忽視文字事工,才為重中之重。
七年前,我已向教會及出版界提出:華人教會需關注的幾個問題:“冷眼看當前基督教出版界的失衡現象”一文中論及“教會宣教政策的失衡”,“台,港出版市場的失衡”,“翻譯與創作的失衡”,“福音讀物與靈修讀物的失衡”,“教會刊物讀者群的失衡”與“中文基督教出刊地域的失衡”等(詳2009年由台北道聲出版社出版之拙著悲愴大地p.307)。可惜未引起台,港教會的注意。如今兩地教會的出版物,編,印均已臻上乘,與教會以外的書刊相比,並無遜色。但台,港等地區內卻擠滿了近百間教會出版機構,大家都擠在這塊小餅中爭食,爭得你死我活,但仍然吃不飽。如今窄巷已快被擠爆了,似仍然無計可施。
大家熟知對岸有廣大的銷書市場,其中擠滿了嗷嗷待哺的靈性饑民,都渴望一點靈水沾沾焦敝的舌頭。但大家也都束手無策,趑趄不前。因要進入這塊廣大的市場並非易事。教會的文字事工拓荒者,必須具有冒險犯難的精神,才能突破困境。文字事工從無捷徑可循,古今皆同。
當年諸葛亮在其著名的“後出師表”中勸後主冒險出兵伐魏,因不伐也要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同樣,我再次大膽呼籲台,港出版界:“倘若大家一起同在窄巷中擠死,孰與努力衝出窄巷,奔向另一廣大市場。求神賜給我們智慧與力量,耶和華神豈有難成之事。”(刊於2015年4月基道文字)
其實,我在此要與諸位共同勉勵的是:一個文字工作者,如何才能做一個忠心的管家。以下引證兩段經文: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祕事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哥林多前書4:1-2)
“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啟示錄2:10下)
諸位同工,無論在教會或教會機構中任職,都有一定時間的任期。但若一個人要獻身作為基督教的出版人,或文字工作者,除世上的體制外,應以終生為任期,要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語出諸葛亮“後出師表”的終身奉獻精神,如同早期的一些文字工作傳教士們(如李提摩太等人)。按諸葛亮出師應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他揮師北伐,七出祁山,卻未能生還。杜甫有詩詠之:“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你所立足的這塊領域,有無止境的挑戰;如中途退出,或將前功盡棄。而這頂生命的冠冕也十分沉重。據悉英王加冕之冠,上面鑲滿了寶石珠玉,十分沉重。加冕時,上面要由高處懸下一條鋼絲繫着,受冕者頭部才可以承受。那是由於地心吸力的重量。但生命的冠冕則為屬靈的重量,必須要時時刻刻,求神加添力量,才能勝任愉快。孟子曰: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我們都已看到了基督的榜樣,但我們當然不能與基督相比。主說:“要背起你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潘霍華解釋為:“基督呼召你,就是要你去死!”難道跟隨主是死路一條嗎?當然不是。潘氏繼續解說:“你只要願將十字架背起來,便會感到輕鬆了。因為靠着那加給我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保羅要我們做執事(僕人)及奧秘事的管家,甚麼是神的奧秘事呢?保羅有十分清楚地交代:“我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哥林多前書2:2)所以背起十字架來傳福音,就是上帝救世的奧秘。
做為一個文字工作者,一位出版人,同時也可用各種媒體宣教,不同的事工雖千變萬殊,但只要不離開基督的十字架,都應相同。一旦遠離了十字架,便遠離了救主的福音。以文字事工宣示十字架救恩,正是一個出版人的終身志業。
我在從事出版工作時,因應教會的種種需要,也兼做了一些多媒體的傳播事工,無論做任何工作,最後都會再回到文字出版。一個出版人無論做甚麼事情,都必須以文字事工為他的中心與重心;如讓文字事工多元化,或E化,也都不違背當初神給我們的異象,這便是出版人的忠忱。
由“小書齋”到“百合書屋”的種種辛酸
我由文字工作職場卸下重擔,感到極端無奈與疲憊,但還有一批批粉絲們紛紛前來向我致意與慰問。其實多半是要向我投資,要我換個環境再出發。他們所看重的,多為我對當時出版市場的影響力;所着眼的,無非因我可能創造的市場利潤。但那些並非我從事出版的初衷。這些人中,有一位是當時某著名大公司的CEO,還真讓我受寵若驚了。
他們都看走了眼,完全站在與我相反的方向,使我更感無奈。我放下“道聲”後,已由“壓力山大”中脫出身來,多麼想好好呼吸一口“自由”空氣,歇一歇。若還想繼續在教會外從事僅為牟利的出版,豈不是迷失了自我?我向這些好心人們表示感激,但我也表明:十分慶幸脫離了這個職場,正想休養生息,再等候神的差遣。我決不會僅為利潤而出版;若然,我又何須資金。以我當時在出版界的影響力,根本不須用資金;因為出版市場多半相信我推出之書,必會暢銷。先賒欠紙張與印刷費即可出書,因在短期內,費用便可回收。只要租一間辦公室便可開始,願意自動投效的編輯們,也會響應歸隊。如果當時合了投資者心意,那“我”還是我嗎?
不久,我便打包行李(主要是我三次搬遷後存留約萬冊圖書),還與一些人合租了一個貨櫃,才將大部分圖書運至居住地。我在金山海濱不遠處,覓得棲身之所,安頓下來,也在當地一個教會做義工。暇時便進入我的“小書齋”,拾起從未染墨的毛筆揮毫,回到我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墨香天地。我生平最喜愛翰墨,但在台北時,除教會工作外,已將全部時間交給了早期篳路藍縷的出版事業。我每晨七時到辦公室,先燒一壺開水,為自己與二樓的同工們沏上一杯茶,再開始工作。晚間七時後離去。每天工作約十二個小時。身兼數職,權充一個全職出版人:包括選書,編書,審稿,美工,及校對等等。等到出版社能站住了腳,我的作息習慣也未更改,直到離職時為止。有時回我牧養的教會,剛剛可以趕上晚間聚會,故只能在九,十點才進晚餐。
我購買了許多法帖,包括歐,柳,顏,趙,蘇,黃,米,蔡等八大家以及許多古今名家的字帖,擁有各式法帖約數百種。歸隱後,每天多半與翰墨為伍,揮毫不倦。進入我韜光養晦的墨香世界。
但十年也磨不出一劍,諸書法大家中,黃庭堅為我最愛,幼時即曾習其“梨花詩”帖。黃字如幽蘭般伸卷自如,毫端起落,皆恰到好處。但後來我購買的“梨花詩”帖,都遠不如幼時家中的藏帖。黃氏此類書法,也僅“梨花詩”一帖而已,其餘帖筆法皆不同此體。但久習仍難得其神韻,因改習趙子昂,蘇東坡等大家。米南宮與趙孟頫神態皆難捉模,略得其梗概而已。
後再改寫清代書法大家鄭板橋體,對其六分半,亂石鋪街書法之“打鬆美盤得大自在”意境,頗為欣賞。其書法能顛覆歷代常規,獨創一格。我曾將其論書法諸帖,浸淫多時,略諳其用筆之三昧,並將臨摹的多幅字跡,裱裝成數十丈長卷。
間有人索書,故習作外流者不知凡幾。或有人言:“某人習鄭字已可亂真,其作品應可收藏了。”皆為過譽之詞,因知我者,莫如自己的禿筆也。
習字許久後,倦於筆墨,再拾讀古詩文集,神游諸子百家典籍中。同時更潛心研讀新舊約聖經,每發掘出經中奧義,便寫成心得,再印成書卷。計先後陸續出版習作二十餘種,多移為大陸文字事工之用。

獄中的保羅
St. Paul in Prison, 1627
Rembrandt Harmensz. van Rijn 1606–1669
幸爾我還能深深體會保羅所講:“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如我比較約伯的遭遇,實在為“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哥林多後書四:17-18)“一粒微塵”之信心,尚不如微塵,但神的恩典卻遠超世上一切塵埃。哈利路亞!阿們!
作者殷穎牧師剛於2018年九月二十日安息主懷。本期選載其自述文字事奉歷程之文章,以表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