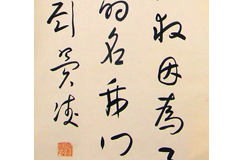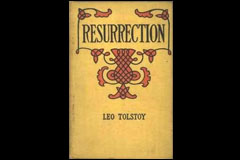政教關係的糾結
宗教是藉由信仰的力量,影響人民的行動。政治也是要影響人民的行動,不問其信仰,必要的時候,要經由法律的約制。大部分的原始民族,其部族首領也就是祭司,兼理宗教與政治。在中國,君王稱為“天子”,是“奉天承運”;換句話說,他就是信仰的對象,也就是構成宗教的主要部分。
中國的傳統是敬天,天唯有一個,惟天則之,當然該是一神信仰;不過,又因為這天是以人為代表,所以也可說是沒有宗教,或人本的宗教。
先秦時期,百家並舉。可是,他們都不稱為宗教,也少談到有關宗教信仰方面的事。經秦統一中國,及漢代秦而興,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張陵就附會道家,衍生道教。後來更被俗化利用,成為五斗米教;更因政治窳敗,張角等人興起黃巾之亂,並且聲勢一時頗盛,促進晚漢的衰敗。後來群雄割據,統合為魏晉。眼見儒家修齊治平的理想,經過那麼多年,試而不驗,顯得僅是高調而已,並沒有帶來大同,知識分子有理由失望;人事既然不堪問聞,消極的談天說玄,不趟渾水,自然以清為高。
接之而來的南北朝,更是篡亂相繼,天理人道,都無法講得清,看似陷入迷茫無望。自印度輸入的佛教,提供一個不解之釋:塵網是由於業緣,輪迴生死,在團團不絕的打圈子。這樣,不必真正對自己的作為負責任,形成道德的相對論。在實際生活上,佛教的僧伽,有他們的禪林名剎,應該安分於遯居山野,不染紅塵;但受他們有的不僅干政,還榮受“國師”之尊,並不會缺乏史例。
唐太宗早年的作為,使他有理由內疚。雖然道教認老子為先祖,李耳成為皇家的同宗,享有相當方便;但太宗有些像聖經中的古列王(居魯士),對不同宗教兼收並容,以為都能增福,因而多多益善。太宗不僅接受輸入的佛教,也兼收並容各宗各教。所以景教東傳到華,太宗就差代表魏徵出京都長安郊迎,歡喜接受為官方宗教之一。景教的教牧稱為“景僧”,享受禮遇。以後的皇帝也加以寵眷。到安史之亂起,郭子儀率兵平亂時,景僧則積極參與,“為公爪牙,作軍耳目”(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是指中亞以西的人。想來高鼻深目的波斯人,不太適合作政府軍的偵探;不過,那時中西交通普遍,各色西方來的商人不少,在中國不太受歧視。
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歸信基督教以後,羅馬統治下的歐洲,成為所謂的基督教國,至少理論上是政教合一;可是,歷來爭競不息:一方面想以教統政,以為領主不過是一名平信徒,應該順從教皇,因其為基督的代理人;領主則企圖以掙統教,視教職人員為其屬民。他們兩方並不需要如此聲明,但隨其勢力此消彼長,情勢變化,總是政教不協;及至回教興起,乘機迅速發展,占據了猶太和聖經地區。到了十一世紀,政教達成了某種協調,組成所謂十字軍,藉口幫助恢復基督教失地,進行其“武裝朝聖”的東征。而究其竟,動機十分複雜,成員也各色人紛集。如眾所知,後果也頗不理想,幾乎可說乏善可陳。
十字軍形成的社境,與中國的黃巾賊,像是“門當戶對”,其利用宗教,頗不乏類似的地方,不過約晚了千年之久。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使歐洲列國形勢更加明顯。

烏爾錫
很可能是看到這類現象,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說:“宗教,不管甚麼宗教,對於一般人,都是同樣的真實;對於哲學家,都是同樣的虛假;對於執政者,都是同樣的有用。”不過,真正的宗教,對於真正有信仰的政治家,應該是施政的引導和準則。這是我們的期望。
(同載於聖經網 aboutbible.net 之“天上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