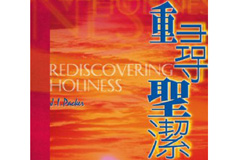春天到了
一個奇異的思想,突然閃亮在我的心中,“春天到了”。
當這個信息在我意識中出現的時候,我的確有些奮揚與激動,但隨之又平靜了。我現在已不再有孩子時的那股勇氣,丟下所有的功課,將書本拋上半空,無掛無礙地投進春天的懷抱,去吸吮春天的奶汁,任春風拂弄我的頭髮,讓花瓣親吻我的腮頰,聽燕子帶來遙遠的童話。
“唔─春天到了…”我的腿由椅子上彈起來,但手中仍然捏着一本與春天極不和諧的哲學概論。我做了一個聳動的姿式,但當我用怯怯的眼光看了看坐在周圍道貌岸然的君子們,我再也不敢將手中的書本拋出去,而兩條滯重的腿也沒有勇氣衝出房門,終於我用慢吞吞的,很有修養的步伐踱出了門檻。一隻手將那卷哲學概論掩在背後,抬起另外的一隻手來扶正了鼻上的近視眼鏡,由一圈圈的深度的鏡片裏,看見了樓下開得火紅的杜鵑,與綠得惹眼的蕉葉。抬頭望了望白雲拂拭過的明淨的藍天,孩子們追逐的笑聲,與啁啾的鳥語,輕柔地傳入耳際。在我不太靈敏的嗅覺裏,嗅到了春天特有的氣息。
我聽到自己唔了一聲,惘然地重複着那句對春天毫無意義的話:“春天到了”。
其實,生活在春天裏的孩子,並不覺得它是春天。只覺得它是一個最知心的朋友,一個最玩得來的夥伴,因為孩子是春天的,而春天也是孩子的。等到長大了幾歲年紀,“懂得”欣賞春天,再學會了舞文弄墨,寫一首詩,或填一闋詞甚麼的,自作多情地對“春”發揮一份情感,謳歌讚美上一通,高興了也許還灑上幾滴眼淚,用些矯揉造作的詞藻,說出甚麼“惜春”“傷春”的傻話來。硬將自己湊進騷人墨客的數裏,而實際上已經斫喪心靈中青春活潑的生機,已經從春的國度裏被放逐出來了。
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園序”中寫的“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以及清平調中“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的詩句,將春天寫成詩文,着了筆墨的痕跡,落了言詮。儘管詩文的境界與創作的才華是絕世的,但畢竟還是在春之國度以外的手筆啊!
春天真正的寵兒是天真無邪的孩子們,他們不會寫詩,但他們本身是詩。他們不會作畫,而他們自己是畫。他們是春的細胞,春是他們的整體。他們追着春風跑,他們倒在地上滾,他們和溪水一同歌唱,他們與蝴蝶一齊飛舞,他們與春天同一個鼻管呼吸,同一個心臟跳動,在同一個膨脹的生命力裏向外奔放!
看到那些在春風中追逐的寵兒們,不覺由心中升起了一股酸溜溜的滋味。
“唔─春天到了。”如果一想到它,馬上喚醒了兒時的回憶,拾起兒時的心情,硬擠到孩子群裏去分享一點春天的生命,也還無傷大雅。最糟的是一想到“春天到了”便惹起了無邊的憂鬱,想起故鄉春天的種種,害起思鄉病來。硬將春天分割成“故鄉的”與“異鄉的”。然後又情不自禁地傷感起來,詠嘆起來,將明朗的春天染上了沈鬱的調子,才大煞風景呢!
那些被棄於春天之外的人們,偏偏最喜歡“煞風景”,以“春天”為題,在詩人手裏便會寫出富有羅曼蒂克的香艷纏綿的詩句。在小說家筆下也許會寫成男女戀愛的故事。在哲學家的觀念中會想到宇宙的本體。一個報紙的主筆能運用一些政治的術語與經濟的詞彙寫成一篇國計民生或展望世局的社論。而在一個商人的頭腦裏,則是如何設計一個招徠顧客的“春季大減價”的廣告…總之,失落了青春生命的人,又怎可以與語春天呢?
春天是孩子們的,孩子們是春天的!
當這些由春天的國度裏被放逐出來的人們,在咀嚼着“春天到了”這句話時,心裏面實包含着許多說不出的辛酸,失意,嫉羨與無可奈何的惆悵!![]()
本文選自作者散文集歸回田園。
台北:道聲出版社
(10641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15號,電話:(02)23938583)
(書介及出版社資訊:http://www.taosheng.com.tw/bookfiles-10J/bookfiles-10J025.htm)
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100028北京市朝陽區西垻河南里17號樓,電話:(010)64668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