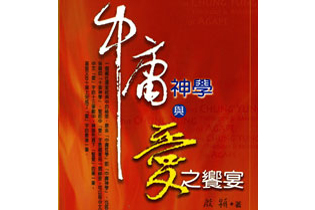讀書樂
謀奇維利與李宗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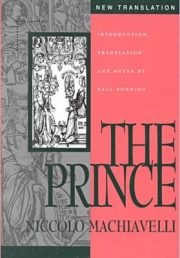
謀奇維利(Niccolo Maciavelli ,1469-1527)的名著君主論(De Principatibus, The Prince)於1513年作成,到他死後五年,1532年才出版。
他崩逝以後,不過半個世紀,名聲就遍傳歐洲;有美譽,也有更多反對。有人稱他天縱睿智;有人說他是受魔鬼啟發。君主論為教廷列為禁書;但也有人奉為圭臬。
在英國劇作家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所作馬爾他的猶太人(The Jew of Malta, 1591)“序幕”,謀奇維利出現說:
愛我的人謹慎不宣於口,
讓人知道我是謀奇維利,
不要衡量人,不要信人的話。
敬重我的是最恨我的人。
那些公開反對我著作的,
他們讀我的書,因此爬上
彼得的寶座…
可見他早已經確立政略家的負面形象,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道地的陰謀家。多少年來,大致一直是這樣。
其實,這樣衡斷是否公道,似頗可懷疑。
謀奇維利生在弗羅稜斯,曾在政府任過要職,包括外交職位。到出過教皇的當地麥迪奇(Medici)豪門當政,才把他免職,並且曾入獄及受刑。以後的歲月,他就自己閒居種菜。
他寫給知友,弗羅稜斯駐教廷大使韋託理(Vettori)的信中說:傍晚回家,脫卸泥污汗穢的衣服,換上公服,與往古的政要領袖們“傾心交談”,論到他們的權術,成敗得失。結果是君主論。
從這書的內容來看,應該屬於分析評論,較少是政治學教科書的成分。
從著作背景看,那時的意大利,分崩離析,不復當年羅馬興盛;他希望能有一位偉大的解放領袖出現。麥迪奇家族中,當然該產生這樣的人物;如果他的意見得到接納,就業自然不成問題。作者心目中的“君主”,實在與國家不能分開的。
從道德觀念看,既然君主即國家,國家所要的是功利,是生存需要,所以談不上“道德”。所以書中也不講道德威力的成分,只講策略重於武力。
從作者心理看,他既得罪於巨室,希望借此書再為進身之階。他的體裁是用特異的文筆。不過,常是看來坦白,細味則別有滋味,諷刺帶些辛辣。可能是故意如此;也許是受到不公平的迫害和冷落,不自覺的流露出心底的苦水。
書中說:君主不必有道德,但該裝模作樣有道德;信義,公平,良善,誠實等,只是裝飾品。君主不必有信仰,必要時,不妨以宗教為外衣。君主應該兼仁愛和威厲,恩威並施;但叫人怕比叫人愛容易,所以要經常用壓力,恩惠只可點滴施予,人民才品嘗到甜味而懷恩。君主應該如狐狸,也如獅子。
他更提醒讀者:必要時,你不妨殺人的父親,但萬不可奪人的祖業;因為殺父之仇可以忘記,而奪產之恨終生難忘。迫害人民要恰到好處,以不激起報復為原則。
謀奇維利把“篡奪”這個詞兒,除去低評的意思,當作平常的手段來平淡的敘述,仿佛是在桌上討論爭議的陰謀。他舉出歷史上許多醜事,惡例,都是教皇,君王,領袖們幹出來的功業,只說其“成功”,失敗,以證明好人沒好報,越自私,越成功。
作者把這本奇書呈獻給“偉大的勞倫斯.麥迪奇”(The Magnificent Lorenzo Di Piero De' Medici, 1492-1519)公爵。但那好大喜功的年輕人,淡然置之。
也許,這書將永遠被遺忘了。不過,那時歐洲新發明了印刷機,才得以傳播廣遠。
本書的論據,過分強調人性的惡,以羅馬為宗教的代表,所以完全看不到救恩的亮光。出版的時候,正是宗教改革運動時期,所以被詆斥為最黑暗的書。但一紙風行,加以列入教廷的禁書名單以後,更助長人的興趣;買到人視之為“秘本”,珍視誦讀,影響也就更大。
幾個世紀後,東方的獨裁者,也聽到了此書。不知是逢迎的人翻譯了邀功,或是領袖着心腹祕密翻譯,成為“統馭術”的秘本珍藏。
如果說,君主論給人的印象,是狐狸和獅子:“凶狡”範型,中國也有人著論“厚黑”。其對象不僅是君主,而是一般大眾。不過,從其立論的基礎看,也是採取歷史名人的事例,似乎是君主論的普及本,只是簡化了許多;取例少,篇幅短,理論淺,影響也小,當然,其著述的時代背景,也有些類似。
那就是李宗吾的厚黑學。
李宗吾生於光緒五年(1879年)。祖先原籍廣東,後遷到四川富順,所以是四川人。本名世銓,後改名世楷,字宗儒。入四川高等學堂,至二十五歲,思想大變,不滿意儒教;心想如其宗法孔子,不如宗法自己,遂改為宗吾。
據他自己在“厚黑叢話”中說:
著者於在滿清末年,發明厚黑學,大旨言一部廿四史中的英雄豪傑,其成功秘訣,不外“面厚心黑”四字,引歷史事為證…這本是寫來開玩笑的,不料從此以後,厚黑學三字,竟洋溢乎四川,成一普通名詞。
可見他研究的方法,與謀奇維利相同,只是範圍較窄,說理較淺。所不同的,是那時已經有報紙,一經刊載,立即引起人的廣泛注意。
他本來不是想開宗立派,建廟施教的,後來卻發展成“厚黑教”,著作“厚黑經”,“厚黑傳習錄”,“厚黑史觀”,並如何求官,如何作官,及“補鍋”,“鋸箭”的辦事妙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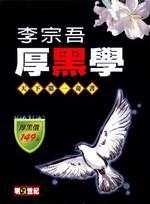
他自己說到厚黑學的著述目的:“用厚黑史觀,去讀二十四史,則成敗興衰,瞭如指掌;用厚黑史觀,去考察社會,則如牛渚燃犀,百怪畢現。”
這位教主又說:“用厚黑以圖謀一己之私利,是最卑劣之行為,越厚黑,人格越卑污;用厚黑以圖謀眾人之公利,是至高無上之道德,越厚黑,人格越高尚。”所以他標榜“厚黑救國”,並說:厚黑與救國,融合為一,是之謂“中國魂”。
李宗吾並沒有教出一批惡人誤國亡國,也沒有喚醒國人救國強國。因為沒有誰認真倡導,他也不是當權者,不能強制人民研讀他的訓詞,語錄,更沒有機構替他推銷;結果只是知道的人,當作譏諷的語詞。
但他說:“讀者見了我的厚黑二字,把他譯成正義二字也可,即譯之為道德二字,或仁義二字,也無不可。”
至於李宗吾本人,並不是面厚心黑的人物。據認識他的人說,他還被自己的學生騙過,甚至連長袍也脫下助人。所以他是說得出,作不出的人。
他又說:“天下事有做得說不得的。”既是“說不得”,不是由於太黑,就是臉皮不夠厚了。所以只好拉出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來自圓其說了。
不過,他的努力,也影響了些人。李說:
許多人向我說:“把你發明的原則去讀資治通鑑,讀了幾本,覺得處處俱合。”我聽見這話,知道一般人已經有了厚黑常識,程度漸漸增高。…
後來的李敖,也有可能是受到啟發的人之一。
謀奇維利與李宗吾等人,有個共同點,就是對宗教缺乏興趣;他們看到了人性的敗壞,卻苦無救治之道。
聖經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耶穌基督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羅馬書3:23,24)只有神能賜給悔改的人新心,使人的臉改變,反映主的榮光,並能除去自私,愛人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