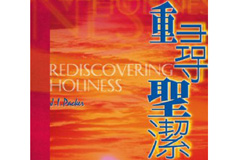人民詩人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唐太原人。他自幼聰慧,五歲即能作詩。因為父親逝世,家道不豐,遲至二十七歲,始得應考試,舉為進士。後由翰林院,而出為蘇州,杭州刺史,內調為刑部侍郎,並擢尚書,授太子少傅。退休履道里後,號香山居士。
他雖然歷任官職,但與當時的文人不同,所寫的詩平易近人,不識字的老嫗都能夠懂。他的詩,常寓道德教訓於文藝,譏刺社會病態,諷諫時弊,可稱為平民詩人。
他的“新豐折臂翁”,是反戰文學的先鋒。開始介紹詩中描述的主角說:
新豐老翁八十八 頭鬢眉鬚皆似雪
玄孫扶向店前行 左臂憑肩右臂折
問翁臂折來幾年 兼問致折何因緣
詩人不是宣揚他自己的意見,而是記載偶然遇到的人,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你不妨說他是個不名譽的人物;但從這人物的口中,說出一個不平常的故事。
人老了,右臂折斷的殘廢人,坦白的敘述他悲劇的故事。故事發生在詩人出生前二十年,唐天寶十一年,楊國忠憑妹妹是皇帝寵愛的貴妃的關係,當上了宰相。這位既無才,又無德的新貴,除貪污弄權一無所長。為了建立自己的聲威,找個借口要去征蠻立功。那時候,甚麼借口都行,就算是弄蠱吧,那是“集體毀滅性的武器”;邊民為一隻雞,或一頭豬的爭鬥,習慣上叫作蠻夷入侵,也就可以發動征兵,以進行討蠻的戰爭,出師有名,可以發國難財了。
翁云貫屬新豐縣 生逢聖代無征戰
慣聽梨園歌管聲 不識旗槍與弓箭
無何天寶大徵兵 戶有三丁點一丁
點得驅將何處去 五月萬里雲南行
聞道雲南有瀘水 椒花落時瘴煙起
大軍徒涉水如湯 未過十人二三死
村南村北枯聲哀 兒別爺娘父別妻
皆云自古征蠻者 千萬人行無一回
今天的八八衰翁,說到六十四年前的往事。當年他二十四歲,是陝西新豐縣的一無名青年,他沒有抗議的能力,只有抱“毒蛇囓腕,壯士斷臂”的精神,壯烈的自殘肢體,逃避兵役。詩人顯然沒有大義譴責他不愛國,畏怯偷生。國家已經被貴戚官僚竊據了,“愛國”的美名,成了殘害百姓的假幌子,在“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動機驅使下,愚昧的甘作無辜的踏腳石,算不得甚麼英雄。
是時翁年二十四 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 偷將大石搥折臂
張弓簸旗俱不堪 從玆始免征雲南
骨碎筋傷非不苦 且圖揀退歸鄉土
此臂折來六十年 一肢雖廢一身全
至今風雨陰寒夜 直到天明痛不眠
痛不眠 終不悔 且喜老身今獨在
不然當年瀘水頭 身死魂飛骨不收
早作雲南望鄉鬼 萬人塚上哭呦呦
逃避入伍的老人,不恥自己的畏怯,慷慨也悲哀的述說自己智慧的決定。我們想見他撫着俊美玄孫的頭,仿佛說:你的父親,祖父,曾祖父,繁衍了三四代,開發了土地,增加了農產,滋長了經濟,都是因為我這條右臂的代價!
正直敢言的詩人白居易,冒着犧牲政治前途的危險,記下了假愛國主義的罪孽:
君不聞
開元宰相宋開府 不賞邊功防黷武
又不聞
天寶宰相楊國忠 為求恩幸立邊功
邊功未立生民怨 請問新豐折臂翁
白居易為人正直,忠鯁敢言。他聽了新豐老翁的見證,動了義憤;本來是記事的詩,他跳出來作起評論。他不是不知道這樣會損害詩,而且會招怨,但不能不說。
他說到開元時的賢相宋璟,安文求治,愛國愛民。他抑制好戰喜功的郝靈荃,不使他達到升官侵略的目的。唐玄宗將老寵幸楊玉環,封為貴妃;為裙帶關係,“兄弟姊妹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貴妃的弟弟楊國忠為相,為了聲望不孚,急圖立功,找機會出兵征蠻。徵兵的辦法是強行抓丁,捉人連枷赴役,前後發二十對萬人民。他不像諸葛亮為國忠心,與軍士同甘共苦,“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他只是讓平民屈送死,高官子弟沒有當兵的。這樣,欠缺計畫,供應不足,要未經訓練的百姓,在炎熱的天氣,沒有舟楫渡瀘水,水像沸湯,兵丁在惡濁的水中倒斃,好好的年輕人,有去無返者。天下怨哭,人不聊生。安祿山乘政府失人心而起,人民不是愛安祿山,而是恨楊國忠,紛紛反唐,幾乎推翻了李家政權。
此詩約作於唐憲宗元和十一年(816年)。
低卑逃役的人,哪能知道上前線的艱苦?今天,科技進步了,戰爭的方式不同了。連美國這樣的國家,遣發去國外打仗的,也少有高級政府官員的子弟,所以受不到好的照顧。他們不過是“以血換油”的籌碼,多犧牲幾個,又有甚麼了不起!
被送出去的人,撇妻別雛,為“莫須有”而戰,而屠殺同類不同膚色的人,既有良知,心靈能不內疚?所以不僅有數不清的“折臂翁”,是自己傷殘肢體的結果,也有許多自殺的。有時候當政者聰明,單方面宣佈勝利,趕快向後轉再前進,運氣好活着回到本國的兵,也都變了。有個母親說:“我的兒子去打仗回來,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據調查:有三分之一是嚴重精神失常,吸毒自我麻醉,或竟作出各樣反常的事,傷害別人或自己,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盼望有人能寫下今天的“新豐折臂翁”故事,給當政的人學些功課。
白居易還有描寫上層社會的詩:
秦中吟“輕肥”
意氣驕滿路 鞍馬光照塵
借問何為者 人稱是內臣
朱紱皆大夫 紫綬悉將軍
誇赴軍中宴 走馬去如雲
樽罍溢九醞 水陸羅八珍
果擘洞庭橘 鱠切天池鱗
食飽心自若 酒酣氣益振
是歲江南旱 衢州人食人
這樣盛大的“軍中宴”,是怎麼來的?
春秋時,開始有以權臣監軍;漢以後沿用,有時以御史監軍。唐開元時,開了以宦官為監軍的例。因此,軍事領袖要看內臣的顏色,內臣就影響軍隊系統。內臣近“天顏”,當然會關係皇帝將領們的寵眷前途;軍門是最有錢的機構,皇帝要買將領的忠心,國防預算佔了國家開支最大的項目,誰要反對出錢就是不愛國,那還了得!不過,有了錢是一回事,怎樣支配是一回事,不一定落到兵卒的身上。將軍們和宦官們,在歌舞歡樂,慶祝甚麼領袖就任,享受山珍海味,美酒佳餚,食飽酒酣;他們吃喝的都記在軍事預算上,實際上是民脂民膏,老百姓的血肉,連骨頭都啃光。加上遇到連年旱災,人民給餓到枯瘦,活不下去,到人吃人的悲慘地步。
這種內臣和軍頭們自肥,不管人民死活的情形,不讓唐人專美,似乎是宇宙性的,今天仍然如此。今天的大國防企業集團,仍然是最富有的,武器消耗折舊,幾乎是無帳可查,更驚人的,是遇到戰爭,可以大傾銷,有誰知道?而小卒子呢?被騙去解放甚麼地方,卻不保證敵國的人民會捧鮮花歡迎;打了三年的仗,才發現血肉之軀缺乏保護!錢花到哪裏去了?這豈不是白居易筆下的寫照嗎?
如此不知避忌的文人,能夠生存,能夠不被整肅掉,仿佛有些像奇蹟。可是,他深入的思想,淺出的才華,卓然不群,上得皇帝的欣賞。中間階層呢?他有的是文人朋友,像元稹,還作到同宰相;而那時當政的高幹們,也是能寬容,有品德的人物。他更有廣大的平民群眾,喜愛他,擁護他;他的詩寫得很多,在他致元稹(微之)書信中說:“自長安[首都],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據說:遠至雞林國(朝鮮的古名)的首相,也愛讀白居易的詩,願意以百金易一篇。這樣的詩人,在朝中作個點綴,表明大唐還是尊崇文化,豈不是為國爭光的事?
白居易仿佛是當時的“詩御史”,享有言論自由,甚至敢於反戰,反貪,反豪門,連現代“富叫”(不是窮叫)自由的美國,也不得不嫉妒,尊敬他。
但今天的平民詩人白居易在哪裏?古詩人稱為“先見”;今天的基督徒文人領袖當中,不缺乏“太監神學家”,在為當權者捧場,難道就沒有人肯為人民講話?
願今天興起平民詩人,作啞巴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