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愛情與救贖視野
沒有一個藝術家可以偉大到不用經歷屬於他自己個人的生命歷程,也沒有一個藝術家偉大到可以超越他身處的時代。生命歷程與時代,並行的塑造一位藝術家的藝術視野,藝術關懷。
如果要找出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文學作品中一脈相承的關懷視野,那就是“到底甚麼是社會關懷與社會正義”?
個人墮落與社會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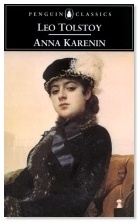
當托爾斯泰開始進行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1877)這部小說時,他關注俄羅斯未來社會的命運的時代視野已經隱隱成形,而他自己,也從一個充滿理想抱負的年輕人,經驗過身不由己的理想幻滅,經驗過愛情與初婚的幸福,與隨後的愛情幻滅,並開始對婚姻中無可奈何的羈絆與瑣碎事物厭倦了。
托爾斯泰本人是個熱愛自然的地主階級。他痛恨貴族階級與軍人階級(軍人階級在俄國也是貴族)的腐敗墮落與虛偽,又對“地主階級是否真的也是造成俄國社會的苦難原因之一”充滿疑慮不安。婚姻的繁瑣也讓他徹底認知愛情與婚姻是兩回事。
於是他決定寫一篇小說,要描述出貴族社會的虛偽腐敗,要描述上流社會一名女子的墮落與死亡,要描述婚姻生活的不幸。
因此,他在小說第一段寫下:“所有的幸福家庭都是相似的,每個不幸家庭都有他自己的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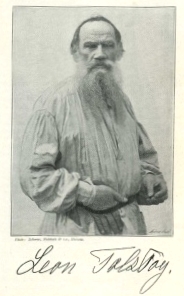
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
寫安娜.卡列尼娜時,他四十五歲,已經有四個孩子,小說寫了四年,從四十五歲寫到四十九歲(唉,我將安娜.卡列尼娜縮寫竟然只用四天…可憐的托爾斯泰…我對不起你…),這四年中間,經歷第五,第六個孩子的出生與夭折。
而這個關注社會正義的人,本來是要控訴上流社會的虛偽腐敗墮落,想要表達對婚姻生活的無奈,誰曉得等小說終於寫完,主題已經變成“當社會對女性如此不公平時,即或當事人已徹底寬宥饒恕並成全,仍無法免於不幸。因此,這不幸社會必得要承擔責任。”安娜.卡列尼娜已經變成一部婦女問題小說,一篇社會正義小說了。顯然的,托爾斯泰透過創作這大部頭著作,自己也經歷了關懷視野的擴大,與心靈的躍升。
究竟是托爾斯泰故意要把上流社會的愛情弄得很膚淺?還是托爾斯泰不擅長處理深刻愛情?還是托爾斯泰對愛情的理解僅止於此?
我們拿杜斯托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1821-1881)後期作品,或斯湯達爾(Stendhal, 1783-1842)的紅與黑(The Red and the Black, 1830)作比較,會發現這兩個作者往往處理愛情時,也讓愛情擁有昇華的向度。杜斯托也夫斯基筆下的愛情,成為最深的對軟弱與罪的接納,男女主角藉由愛情將不堪的自我昇華,彼此成全更高尚的自我。而紅與黑中,愛情成為“單純靈魂”的象徵,男主角歷經攀爬上流社會,充滿虛假權力慾的過程,卻永遠回返最初的愛情找到單純的靈魂。男女主角的心靈交流重要性絕對是大過外貌吸引力的。
從這角度來看,深刻的愛情往往蘊含“救贖”的向度。
但托爾斯泰筆下的愛情卻充滿肉慾。在弗隆斯基(Vronsky)眼中的安娜(Anna),永遠是美貌在吸引着他。連托爾斯泰最寄託以理想的自我表白的列文(Levin),他愛吉蒂(Kitty),也是除了美貌,沒有更多屬於心靈交流的交代。列文與弗隆斯基的差別,是“自然世界大地之子”與“上流社會社交之子”的差別,他們的愛情觀,卻沒有本質上的不同,甚至他們都曾經一齊愛上一個女人吉蒂,只是弗隆斯基轉而追求安娜,終於幾番周折的,讓列文與吉蒂有情人終成眷屬!
因此,若分析愛情的深刻,我們得看杜斯托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的作品整體而言,就愛情描繪,是屬於膚淺型的愛情。(當然,若比之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1857),至少托爾斯泰筆下的愛情,還算質樸形式,不會在肉慾之上還有很多物化的虛榮。)
完人成為軟弱者無法負荷的重壓
安娜必須離開她丈夫,其實恰好是因為她丈夫後來變得太好,讓她無法承負任何對丈夫的不忠實與欺騙。他丈夫原諒了安娜需要愛情,承認這婚姻其實是上流社會的“政治婚姻”,婚姻本身是一場錯誤。他為了不讓安娜毀滅,甚至建議維持婚姻表面的形式,讓安娜擁有得到愛情的自由。
是安娜自己作不到。因為她丈夫太完美了。
在墮落中自覺羞慚的人,無法從完美的人身上找到拯救,因為深覺不配,甚至,這種不配感,會讓她恨上那個完美的人。
軟弱的人只能從另一個軟弱的人身上找到接納與安慰。
在這一點上,幾乎基督教文學作品中一直不停的強調着,基督形象的寄託,也往往因此是溫柔的女性,而非陽剛的英雄。
而不管是托爾斯泰或杜斯托也夫斯基,他們不僅也強調“經驗過軟弱的人,才能真正安慰軟弱”,甚至會把“軟弱的人會因受不了完美形象的重壓,而恨上那個完美的人”的人性部分刻意強調。其實這部分的人性刻畫是非常寫實的。
關於軟弱者接納軟弱者,我們將會在杜斯托也夫斯基的作品中,看到最完整的,淋漓盡致的描繪。至於托爾斯泰,因為他的藝術作品的基調,是“社會正義如何實現”的問題,所以不管是這部安娜.卡列尼娜,或之前之後的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 1869)和復活(Resurrection, 1899),針對“軟弱者接納軟弱”的主題,都輕描淡寫得多。
我之前有提到,托爾斯泰在創作這部作品時,原本是打算批判上流社會的,因此,弗隆斯基不可能是他自我影射的人物,頂多他透過弗隆斯基與安娜,表白了他所理解的婚姻與愛情。
若追溯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之前的戰爭與和平與之後的復活,那連貫性的思考中一脈相承的人物,則我們必須要提一下列文。
列文,我為了避免縮寫過程中很忌諱的冗長繁瑣,決定不處理。但是,列文才真正是托爾斯泰自我影射的人物,他在列文身上,放了很多他個人生命經歷中的嚴肅思考。
列文是個地主。他面對俄羅斯的貧困,有很多的不安,面對當時徘徊十字路口的眾多觀念的實驗,有很多的惶惑。到底農奴制度需不需要被推翻?地主是不是貧窮之惡的淵藪?若要改變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是要走向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的雛形在托爾斯泰時代已經出現了),還是資本主義?俄國的未來,到底需依賴歐化,還是要找到俄國自己本土的路?改革志士能否代表老百姓的聲音?老百姓的聲音,是不是正確能夠依賴的呢?還有,面對爆發中的戰爭,誰有資格決定俄國該參戰與否?誰有這個資格命令一下,便有人死亡呢?
這十字路的徘徊,多像中國的五四時期啊!
這是托爾斯泰面對自己的時代,所出現的矛盾,因此他透過列文,把他摸索思考過程中的種種複雜面向呈現出來。列文與各類代表人物對話,對話中處處反映着矛盾,托爾斯泰沒有透過列文清楚把答案說出來,正可以看出托爾斯泰自己也沒有辦法超越時代看見時代性問題的答案。
此外,托爾斯泰因着哥哥的死,一直思考着生死大謎。面對死亡,生命的意義是甚麼?是緊抓住手邊的幸福,擁抱腳踏的土地?還是不為自己活的,把最精華的自己貢獻給社會?
會出現這個矛盾,是因為托爾斯泰自己真的曾經以地主之身投注農業改革,卻因農奴不信任而徹底失敗。托爾斯泰在改革失敗後,竟因過度幻滅而耽溺於吃喝嫖賭,後來被大哥帶往高加索(Caucasus),面對當地大自然之美與樸實的生活,終於找回心靈的寧靜。他也曾以理想的心,參與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3-1856),卻差點死掉。
所以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就在大自然之美,生活的樸實與徹底入世進入理想主義知識分子群中徘徊,也在死亡之謎與生命意義中徘徊。
儘管面對時代議題,托爾斯泰是矛盾的,但托爾斯泰還透過列文處理遠超越時代,進入永恆向度的信仰議題。
列文是個無神論者,因為當時代,無神論科學主義把知識分子階層的信仰衝擊得體無完膚。
但是當列文置身大地,面對土地上的百姓與自己的人生,又很疑惑,人怎麼可以沒有信仰的生活?
當列文娶妻生子以後,這種周而復始的生活,更讓他急於追尋到永恆的心靈皈依。
他曾經透過哲學尋找答案,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都曾短暫的安慰過他,但是,當他一面對現實生活,哲學就變成一件不溫暖的棉布衣服似的,讓他瓦解了。他又從神學中探討,卻因為各神學家互相抨擊而困惑了,又從教會史中,看見正教歷史和天主教歷史各自認為自己本質無誤而互相否定,更加覺得厭惡。
這種尋找答案的強烈渴望,讓列文越來越痛苦。他無法控制的經常在生活中,工作中出現這些思想:
“不知道我是甚麼,並且我為甚麼在這裏?我怎麼能這樣生活下去呢?”
“在無限的時間裏,無限的物質裏,無限的空間裏,形成了一個泡沫有機體,這個泡沫經過一段時間就破裂了,這個泡沫便是我。”
有時候,列文望着跟他一齊工作的農人,就陷入沈思:
“現在她在打穀場上用勁的踏着曬黑的光腳,但是今天或明天或十年以後,她會死,家人埋葬她,她甚麼都不會留下來。另外那個費道爾也是,現在大聲吆喝吩咐,不知甚麼時候就被埋了。最重要的是,我也會被埋,甚麼也不會留下來。那我是甚麼呢?為甚麼要生活呢?”
這樣的問題一直困擾列文,幾乎讓他想自殺。
直到有一天,還是一個質樸沒知識的農人點醒他。他正在跟列文談天:“米丘黑搾取別人,為自己賺錢,他不可憐人…佛卡內其伯伯,人欠了債,他卻放人走,他不逼人。”
列文問:“為甚麼他們這麼不一樣?”
農人回答的天經地義:“這就是人人不同了。米丘黑只想填飽自己的肚子,但是佛卡內其為他的靈魂活着,他心中有上帝。”
列文着急的問:“你怎麼知道他心中有上帝?”
農人還是回答的天經地義:“這是明顯的,因為他依從真理,順着上帝的意思。”
用腦袋的人找不到上帝,大自然之子,卻會分辨,從善良中找到上帝信仰。這麼簡單的讓善良走入生活,用善良認識心中的上帝。這讓列文徹底醒悟:
“我心中根本就有上帝,因為我一直努力活得善良。為何我還那麼努力的去尋找呢?祂早給了我生命的意義,只是我從來不相信祂在我生命裏。”
當列文用力思想,真理離祂很遠,當列文按善良生活,他在生活中看見真理。現在他的生活,充滿了善的意義。
從這段對列文的描述,我們看見托爾斯泰是如何的透過列文想要幫自己找到答案。
托爾斯泰的小說,都是“文以尋道”的過程。也正好是急切於尋道,托爾斯泰太過於強烈的整理列文的思想,導致只要是列文出現的地方,情節與小說人物刻劃,就都“停擺”,當托爾斯泰越是用力的想把列文的思想攤在讀者前面,越是犧牲掉文學中應有的藝術性,成為思想性的論述文作品了。
列文這個人物,因此若純就藝術角度來審視,是拙劣之筆。但我們卻可以看見托爾斯泰這個文學泰斗的心靈與思想。看見他是如何願意相信大自然質樸百姓身上的深刻,相信這些深刻是“活出來”而不是“說出來”或“想出來”的,相信質樸百姓身上源源不覺湧出的善良,道德力量,相信是他們把人性中最好的那一面,與價值信念,以最質樸的方式保存下來。
所以托爾斯泰是個民粹主義者。這最終導致他成為所謂的“無政府主義”,並不停的批判教會體系。
而托爾斯泰這種對於“從善良道德中看到上帝”的信仰觀點,也將鋪陳復活這部小說的情節主軸。當然,這更是關注社會正義的托爾斯泰,為何不像同樣是關注社會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般在最晚期寫出浮士德(Faust),卻寫出最晚期的作品復活的重要原因。
這個列文,在戰爭與和平中的德烈與畢瑞中,可以看到其前身;而在復活中,也看到列文,畢瑞,德烈的延續與誇張化。最後看到托爾斯泰為自己透過創作找到的信念,做出對自己這一生最大的背叛行為—放棄自己的階級,徹底與基層老百姓認同,以其八十多歲高齡,徹底走出貴族身分的負咎感—這是面對窮困的質樸百姓,他一直無法揮去的罪惡感。![]()


















